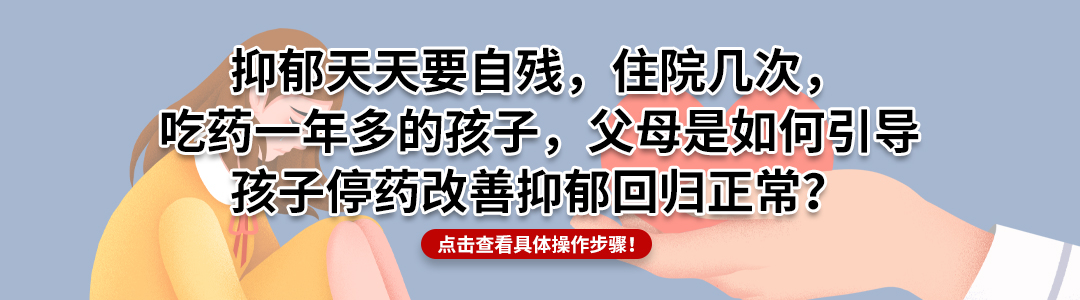這更像是一萬年積存在地殼里的什么成了精的邪惡氣體,其能力不可預測,脹得地表好難受,肯定會找到個泄氣孔。否則的話,這種沉默越想安穩會變得越發困難,會不會最終導致死亡。意思是會導致一場大規模同歸于盡。其滅絕會真正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呢,我們所指是存在著的,而不是虛無,從一個維度進入到另外那個維度,生命快樂,依照規矩就會無止境。
白色小蛾子你現在又飛過來了,掉落在他們眼前的長著苔蘚水泥地上,而這一只會不會就是從前那只呢。能夠揣度造物的用意么?就在月亮的背面到底會上演哪些故事。白樺覺得焦慮,他感覺到從惡夢中掙脫出來后的軟弱,如同虛脫,汗流浹背,甚至撐不起腰。而白樺本人卻處在無限荒謬的境地。白樺當時想起了一個關于高山滑雪的夢來,大地上鋪滿了的未必就是雪粉,或是堅硬如鐵的冰,還有可能是白色塵埃,人會在途中不幸陷落。是的,掉進陷阱去!遠看著那些人影兒(古人猿似的)雙手抓住空中蛛網密布的黑色電線,從七坡八斜山地飛到另外一個山肩上,人影確實就是在飛翔,在起降,遠著頗有些得意忘形,自以為是。他滑到了前面的懸崖邊,山腳下卻有個灰色小鎮,而白樺雙手抓住的蛛絲斷掉了。他的夢甚至還沒有就此打住。他走進一座破破爛爛的石頭宮殿。可能就是他住的客棧。突然看見胖老板娘,她充滿了自信地通知白樺,打算買一輛交通車,在小鎮和那個客棧之間對開,也就是白樺曾生活過的地方。
(場部?龍口大隊?)
隔著大落地玻璃窗一樣,他模糊看得見,迷茫,朦朦朧朧,撲朔迷離,卻顯得他永遠都走不到。白樺霎時間懷疑到時候會不會世界上只有——可能唯獨剩下——他獨自一個乘客呢?聽別人講那個小鎮上發生了襲擊事件,死了好多人,估計是一名長像帥氣的年輕警察不明事由告訴白樺的。白樺好像認得他,他倆勉強算親戚。可能根本不是,兩人之間連任何一種關系都沒有,他就是想強認別個做親戚。
有次白樺參加了一場婚禮,等同于游戲。但是,當婚禮進行到中途時新娘子突然反悔了……譬如說,大家在城市迷了路。
他倆在街道上追來追去,從一條巷子又追到另外一條窄街,整個小鎮(他們農場)現在顯得那么寒冷,除了他倆各自扮演角色的追逐外,便空無一人,就算是在夢里永遠也長不大的白樺同樣感覺到了徹骨的寒意。騷亂就這樣開始了。新娘子的一個表弟本來和他的獄警朋友肯定也是朋友,當時,他從深巷子黑暗底部鉆出來,朝這邊甩了顆天雷。緊接著,子彈嗖嗖嗖在大伙兒頭頂上亂飛。夢里的戰爭就此打響。
白樺在睡夢中奇怪地感覺到已累得精疲力竭。精神病立馬就要發作了。
“連個著力點好像我都找不到。”
“人馬上會飛起來了。”
許多年以后,白樺把夢講給精神病院醫生聽的時候,他輕描淡寫地說:
“那時,我無所依托!”
對門有這樣長滿了水生植物的一大片水域,亮晃晃,閃耀著光斑。他抬起頭,孤零零地凝望著遠方。十分冷漠、霧氣包裹著的無邊無垠沼澤地。最遙遠的地方,連太陽也顯得十分孤單。有一個特別野蠻的力量,在不停地敲打著他的心室,并發出了電波,仿佛強迫他接受,這使得白樺一陣緊接著一陣顫栗。只剩下陰冷白骨鐵硬的一雙大手手爪牢牢地抓住了他。甚至把白樺當場高舉在半空中,簡直覺得,立即就會被撕成碎片。他頑強地抗拒著,歇斯底里,嚎叫,跟幽靈對打。但白樺發不出來任何聲音。他拼命地拌啊拌,拼死地抵抗,直到完全虛脫,根本不能動彈了為止。他看見有個人背影好像是爸爸呀!父親難道說是幫兇?和那些人一樣丑惡。他們果然是一伙的,屬于同個集團。從前就是,將來也肯定還是。突然嘔吐了起來,就像在押送白樺來農場的囚車上,單手銬著,沒哪個逃得掉,所有同學暈車了。他們吐啊吐啊。“他的確是在體制內嘛,現在想起那些人,讓人作嘔。”他告訴J。
對此不知所措,并沒有幻想那么強大,白樺本就是神經質,性格脆弱,天生隨便讓一些欺負,免疫力低,自身又難以把持。夜深人靜時他這樣長不大的孩子偷偷掉出來的眼淚又苦又咸。他告訴四合院朋友自己的遭遇,后來對醫生或精神病院病友嘮叨類似的話,也不管別人聽得懂聽不懂。
爸爸輕言細語說:“樺兒,你坐。你坐。”“你別老是站著。”他對兒子說。
他倆跟從前一樣,當白樺貌似長大了,每當兒同父親兩代人直接交鋒,每一次都是父親先后退小半步。他分明就是故意這樣子干——企圖挑戰父權——讓爸爸反過來安慰自己。出了這可怕的事后,才短短數月,想不到父親的頭發已然大半白了,現在顯得有些蓬亂。天哪,天哪,他眼下的身體狀況會變成了這樣;白樺聯想到,爸爸恐怕再也不能工作到深夜了,他徹底被打垮。當然,他再也不能天不亮就起床,帶兒子跑步,他本人去南明河岸邊的小樹林里打一套太極拳。接見那天爸爸穿件嘩嘰中山裝,白樺知道,來農場之前他可能刻意拿到洗燙店請師傅燙過。“爸爸把來接見當成了一件天大的事!”白樺告訴J說。爸爸彼時就挺直腰坐在兒子對面,顯得裝腔作勢,看上去勉強帶點威嚴,表情卻夠不上算悲憤,他好像并不憂愁。
“非保持體面不可。”白樺接著說。
“有人在窗玻璃后面看著你們。”J表示理解地點點頭。
“他本人也缺少親熱勁。”白樺說。
“更多會迫于壓力。那時情勢。”
“有可能吧。”白樺承認說。
然而,白樺自己就更像是一個局外人。在這院子里現時所發生的一切仿佛與他沒多大關系似的。他命運在他們的掌控中,在那些利害人物的殺伐決斷中,更在叛逆期尾聲男孩與大家所操控的徒勞撥河中。
其實哪一次不一樣呢?從生到死顯然就是這種局面。意思是布局,他焦慮渴望著的脈脈溫情不會出現。
他不會失望。好像,白樺已不習慣父子關系親密了。
這種結果,從來不會單憑人的意志為轉移,總是大圈套著小圈,層巒疊嶂。他倆有時候氣得發抖,卻又不甘心屈服。白樺又一次差點兒就逃掉,從父親掌控中滑脫。他錯誤地覺得,與他們道不同不相為謀。白樺現如今恰好處在從噩夢中剛醒來的早晨——他還遠著呢,并沒有完全清醒——結果,白樺吃驚地發現,私底下,自己在那種環境中潛力被隨便什么人發掘出來,意外變成個準同性戀者,并且有可能對這件事上了癮。依照現行規定算是種病的話,也確實病得不輕。如果讓人發現了就要延期,仿佛是另外一次自投羅網,在找死。何況性格是不撞南墻不回頭——事實上自己恐怕根本回不了頭,誰對誰錯已變得毫無意義——這樣一根筋地跟世俗規范反其道而行(唱反調),白樺本身在潛意識里是否曾動過念頭,就此讓這種人生在適當的時候劃上個句號呢。因為,他十分清楚,確定不能延續后代。彼時白樺知道,所有人(包括假裝正經那種)不會對此容忍,更別說寬容。他倆只不過更像是一個躲在燈光舞臺角落的小丑。如果能夠坦然面對當然好,但真要做到特別困難。老實說,若有朝一日他倆將面對狂風暴雨般的鞭肌入骨責難,很可能現在掉進去了的就是個陷阱,身心俱疲,他又能怎么辦?難道他可以當眾嚶嚶哭泣!白樺即使是不甘心繳械投降,也難以入俗,更不會心安理得。他當著父親面想起了J就更加感到痛苦萬分了。
“你說說看,又有什么辦法喲?”他仿佛在心里邊問過。
總歸是身不由己,也顯得人微言輕啊!
關于這件事情的細枝末節、俗不可耐大概是白樺替自個兒的失魂落魄所暫時找得到的種種借口之一。真相并不對,白樺還是連發語出聲的機會都沒有,任何人不可能給他機會,其中也包括了自己。臺面上所允許的,哪怕當真說出口來也不會是實話,在四合院,連私信都會被別人拆開來看,通過那些約定俗成檢查程序。他更是跳蚤頂不翻被蓋啊!人變成只不過是由得別人隨便捏成什么形狀的一塊泥巴,亂糟糟的軟和面團。所有人貌似在叫花子扭秧歌,傻笑起來就像彩塑泥人。這樣,白樺當初被關進去的時候,失去了的還遠遠不止是他相當看中那種人格。白樺悲哀地感覺到自己還缺失了許多精氣神。
面對給了他生命和肉體的這個長者時,對于白樺來講甚至已經是一個陌生人了。他想起從前他倆除無休止怨懟,其實別無他法。現在,他真的好想順勢坐地上大哭一場。而J又攪和進來。他的女朋友李秋萍反而無影無蹤。她在白樺過往浮躁的生活中仿佛并沒有存在過一樣。那時候白樺更是欲哭無淚。他不再單純是個人,只不過成了關在籠中的動物罷了,任他人參觀,指指戳戳,品頭論足。他們說的什么都在理,到底是如何撥弄算盤珠子,由得別人心情高興。于是白樺突如其來地揚起了眉毛,作為徒勞的反擊手段。白樺大聲說:
“我就知道(他想到‘接見’而不是‘見面’,所以難有對等)場面會尷尬,但任何人絕對不會成功。”
白樺在場部馮政委家大約只呆了小半天功夫,時間對于白樺并沒有完整概念。就他們這種處境(身份)的大部分人而言,只有開始和結束,過程反倒奇怪地被輕易抹掉了,被人為忽略,受到輕視,譬如說完成某種(別人遠比自己更需要的)手續。也就是出生以及死亡,換種慣用說法,是死亡和重生。確實只有兩個節點,才會閃閃發亮。更準確說,常人的觀念,唯一的那次親人接見前后也只有不到兩個小時。他們全都是這種計算時間,必須劃掉路上耽擱了的,浪費在一切閑事上的,或者是,就果真像那個死在青海湖畔的活佛所認識到的那樣,生命全部也就只剩下了生和死,僅僅這兩件事情至關重要。
他心想,自己必須要立馬逃走了。
逃亡。對他來說并不是可有可無,從來也不敢小覷。白樺于是就仍然坐上邊三輪又被人帶回到龍口大隊了。聞到汽油味,五臟六腑抖得心翻,但他這次并沒有再沒事找事地一個勁兒嘔吐。在將要進四合院前,古大隊副又對白樺嘰哩哇啦地說了好些看似意味深長的話,對于他是否有切膚之愛或痛呢?他腮幫子肌肉在不停地抽搐,眼睛死盯住腳尖,雙臂下垂。完全像是打了敗仗的雞。他并且不敢和大隊副眼鋒對接。干部鼻音重濁的那種聲音嘟嘟噥噥地,白樺沒有能夠完全聽得懂。
當他稀里糊涂進了四合院走進牢房的時候天已經黑盡。
先脫掉鞋,打算等洗干凈曬干了再還。羅小松客氣地說用不著洗了。白樺走進J和那些一直在等著他的人當中(他長長地嘆了口氣),看得出來,同類人群發自肺腑地在歡迎白樺此時此刻的一次光榮回歸。他甚至覺得,有幾分奇怪,他們——最主要是J——到底是在擔心什么呢?大大地松了口氣,又能找出來何種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大家確實顯得心神不定、提心吊膽了一整天,事后J和李詳也對白樺承認。
他倆害怕“伴兒”插翅而飛——這些人從此不再是一伙的。
白樺拼命咳嗽起來,一陣猛烈地咳,全身都在打抖,也讓人揪心。好幾個鐘頭來回他坐在邊三輪上,盡管長時間太陽普照,心猿意馬,又要迎風戰斗。白樺好像是感冒了。J到處跑去找,終于找到一塊生姜和紅糖,打算替朋友煮姜茶。他本想抽根紙煙,太陽穴巨烈痛起來,開始淌清鼻涕。白樺甚至咳得也越來越兇。
想了想,他覺得還是不抽煙更好。喝完大搪瓷缸淺褐色辛辣的甜水,他額頭上出了一層細密虛汗。
白樺頭變得不那樣疼痛了。
這時候,一貫神經質的年輕作家頭腦反而更清醒了許多。那種做夢般的場景,疲軟無力的狀態仿佛成為了過去時。白樺沒吃晚飯,卻對大家說吃過了。他坐邊三輪上差點被抖散的骨架,一陣一陣襲擊他的疼痛,清晰、真切地告之此前在場部發生過的那些事。其實,白樺根本沒有胃口。也許他就是中午吃得太飽了。他倒是特別覺得口渴。等回到四合院時間又不再流動。
時間確實是過得格外慢。電燈早打開了,照到的汗珠反射出略帶橙紅色光芒。告訴他們接見時候的一些情況。仔細考慮,的確也沒辦法對人隱瞞。更何況,小半同學都等著,焦慮地期待想了解更多,更詳細真相。大家甚至判斷白樺就快要提前解教了。“是啊,我的印象里邊,”他忍不住對他們夸耀說,“我爸一輩子都沒有這樣講究過。他從來都不修邊幅。”他們四周圍安靜得不得了,白樺對面腦袋瓜太多。“肯定會是這樣。哦,哦哦。”J咂了咂嘴,立即一邊附和他的那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