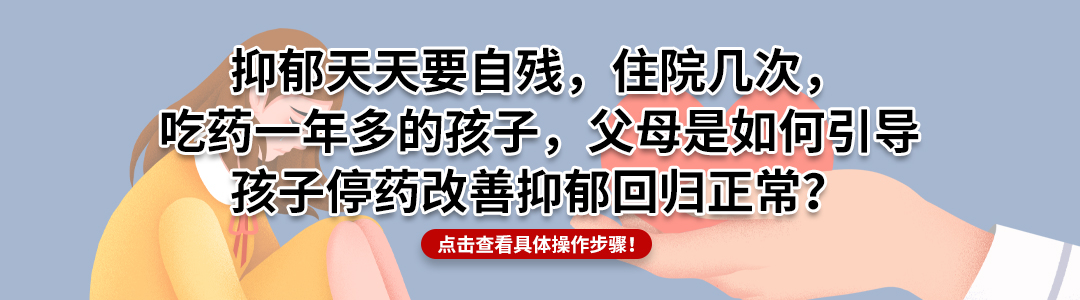當著孩子面說臟話(發現孩子說臟話)
? The New York Times
生活習慣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綜合素質與動手能力,所以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是每一個父母應該承擔的,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在講中華傳統家庭教育直播課里,會系統的講解如何培養孩子的勤與儉,讓孩子能夠按社會準則來去生活,將來出社會工作40年當中,才可以更好的適應社會。
利維坦按:
我們在影視劇里估計看到過這樣類似的橋段:一位大人爆了粗口,然后隨即對身邊的孩子說,這是臟話,你不能學。成年人總是固執地認為,過于幼小的孩子聽到這些臟話似乎會對他(她)的成長不利。想要搞清這一狀況,我覺得首先還是要厘清什么性質的臟話,以及你所說的臟話是針對誰的問題。
我是個滿嘴臟話的媽媽,并且——別嚇到了——我對此并不感到抱歉。關于身為父母卻說臟話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實我在有孩子之前很少說臟話,這有點諷刺,因為一旦你有了孩子,你本不應該在他們周圍罵臟字。畢竟,在孩子面前說臟話是一種禁忌。作為父母,你理應以身作則、言傳身教,誰想聽到孩子罵人呢?
但實話實說,沒有什么比身為父母更讓你有理由罵人了。我每天都會低聲嘀咕好幾次某幾個粗俗的四字母單詞,但在你因此對我進行評判之前,請了解一件事:科學現在站在我這邊。
臟話多少有些益處。
自從人類第一次言說詞句起,人們總是把某些被認為是有害的詞語放在一邊。為什么?因為在一種語言中設置禁忌的詞匯有著重要的作用。假如一頭熊剛剛襲擊了你,或是你踩到了該死的樂高積木——這兩者沒什么差別——那么,尖聲喊道“哦,天哪!”就比不上“特么的見鬼了!”具備那種令人滿足的力量爆發。
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中,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理查德·史蒂芬斯(Richard Stephens)帶領一個研究小組研究咒罵對疼痛耐受性的影響。他們要求一組大學生把手浸入冰冷的水中。他們可以低聲念一段非咒罵性的咒文,也可以隨心所欲地罵臟話。結果發現,和那些說中性語言的人相比,那些說臟話的人的痛苦程度更輕,并且他們把手浸在冰水里的平均時長比前者長了40秒。
(journals.lww.com/neuroreport/Abstract/2009/08050/Swearing_as_a_response_to_pain.4.aspx)
在大腦中發揮作用的是一種叫做痛覺減退效應(hypoalgesic effect)的東西。盡管還未得到完全證實,但目前的理論認為,當大腦理解疼痛時,它激活了杏仁核(amygdala),杏仁核隨即猛地激發“戰斗或逃跑反應”(譯者注:flight or fight response,美國生理學家懷特·坎農所提出,其發現動物機體面對威脅時通常會激起神經和腺體的反應產生應激,使軀體做好防御、掙扎或者逃跑的準備),使腎上腺素在血液中急速流動,幫助暫時減輕疼痛。
然而,問題在于,只有在你不罵太多臟話的情況下,這種奇怪的現象才會出現。因為,正如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樣,重要的是質量而非數量。
科學還表明,在孩子周圍說臟話并不會傷害他們。
你可能不相信,但孩子們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寶貴、易碎的貴重物品。是的,他們需要被愛、被呵護、被保護,但是不知從何時起,孩童之純潔幾乎被神化了:怎么有人敢在他們周圍表現得像個有缺點的凡人一樣?(這真讓人翻白眼。)
假如我們讓孩子們和俗世隔絕,他們要如何學習應對現實世界?我們一致認為臟話和孩子不能共處一室,這已成了一種社會規范。更重要的是,我們甚至制定了法律,懲罰那些敢于不遵守禮儀的人。這是對時間和金錢的破壞性浪費。
2014年,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母親因當眾在孩子面前說臟話而被捕。據報道,當丹妮爾·沃爾夫(Danielle Wolf)的丈夫反復把一片冷凍披薩放在購物車里,壓扁了購物車里的面包時,她感到非常生氣。于是,沃爾夫扔下了一枚“F”打頭的臟字來表達她的不滿。不幸的是,一個旁觀者聽到了這場爭吵并報了警。
當著丈夫和孩子們的面,在一家超市里,沃爾夫當場被捕,并被控告犯有行為不檢。那一刻的羞辱對沃爾夫和她的家庭造成的傷害很可能遠遠大于她在孩子面前罵她丈夫造成的傷害。
正如作家和英語語言專家菲利普·古丁(Philip Goodin)向商業內幕網(Business Insider)解釋的那樣,“臟話之所以會冒犯他人,是因為他人已經做好了(被它冒犯)的心理預期。”他是對的。南卡羅來納州的那位母親之所以會因為在孩子面前說臟話而面臨法律后果,唯一的理由就是另有他人已經預備好被冒犯了。
古丁向商業內幕網解釋說:“這就好像是語言中存在一部分黑暗和邪惡的區域,人們對涉足這片領域十分謹慎,但同時也想踏入其中,或者,至少有許多人想要踏入其中。”他隨后講了一個有關“該死的”(bloody)一詞的奇特故事。
“我記得,應該是在1913年《賣花女》(Pygmalion)首次公演的時候,劇作家蕭伯納使用了這個詞匯,引來了觀眾歇斯底里反應,蕭伯納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他認為演出大概不得不中止,因為觀眾完全失去了控制,而這只是因為一個詞:‘該死的’。我記得應該是伊萊莎·杜立德(譯者注:Eliza Doolittle,該劇女主人公)說了一句‘這該死的不可能’,然后觀眾就崩潰了。”
在2017年為《洛杉磯時報》(LA Times)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認知科學教授本杰明·伯根(Benjamin Bergen)令人驚訝地指出,在孩子面前說臟話并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傷害。伯根著有《這他X的到底是什么:說粗口如何揭示我們的語言、大腦和自身》(What the F: What Swearing Reveals About Our Language, Our Brains, and Ourselves)一書。
伯根指出,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認為說臟話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攻擊行為或致使孩子的正常情緒反應變得麻木”。伯根反駁了這一說法,他解釋說,從來沒有研究著眼于在孩童周圍說臟話的影響,因為讓小孩子接觸臟話是倫理所不容的。
(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128/5/867/tab-article-info)
然而,在大學生周圍說臟話卻是允許的。而且對于伯根來說,他可以輕松地把從關于粗口的實驗中觀察大學生所學到的信息和數據應用到一群幼兒園小朋友身上。那么,他從大學生身上學到了什么呢?
伯根發現,普通的粗口對孩子幾乎沒有影響。但是侮辱性質的臟話呢?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指出,201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反復接觸到辱罵性質的話語最終會改變一個人對受害者和該人自己的感受。例如,在一項觀察性研究中,143名中學生被置于恐同人群的辱罵環境下,最終報告稱他們感到焦慮和抑郁。
重要結論是?
基本而言,你也許可以在孩子面前說臟話。但是你不能懷著仇恨說出那些臟字,比如使用辱罵性質的詞匯或是罵孩子。你的咒罵不能針對特定的人。你不能因為憤怒而抓狂,說出一連串的粗口。
但是,假如你時不時投下一枚“F”字母開頭的臟話炸彈,或是偶爾在走進房間時發現你的孩子剛剛剃光了家里狗狗的毛,于是吐出一句“這特么的是什么狗屎?!”——請記住,你并沒有傷害你的孩子。你只是一位普通的父母。